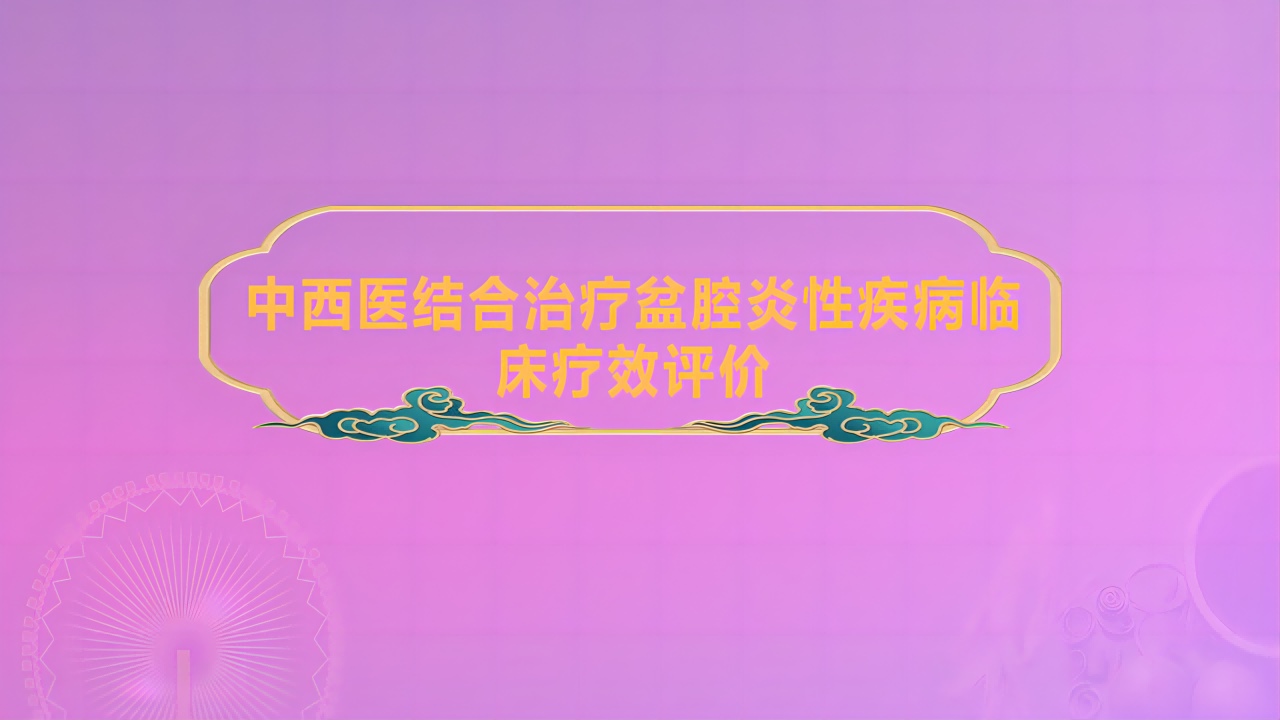医贯中西,指点迷津|天津市中医妇科联盟云沙龙
“定经汤”出自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傅山所著的《傅青主女科》调经篇,主治经水先后无定期之证。傅山先生认为,女科调经尤难,“盖经调则无病,经不调则百病丛生”,在《傅青主女科》中,傅山先生将月经不调分为7种类型,并加论述,对应七方,“用之无不效”,被世人称为“调经圣手”。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副主任、副主任医师、副教授张崴在“医贯中西指点迷津”天津市中医妇科联盟云沙龙中援引古今资料,结合临床实践,对定经汤的组方、方解、功效、临床应用、调经思路等给予讲解。
一、定经汤组成
汤头歌:定经汤用归地芍,菟丝茯苓及山药,柴胡芥穗疏肝气,月经无定服之好。
组方:菟丝子【酒炒,一两(30g)】白芍【酒炒,一两(30g)】当归【酒洗,一两(30g)】大熟地【九蒸,五钱(15g)】山药【炒,五钱(15g)】白茯苓【三钱(9g)】芥穗【炒黑,二钱(6g)】柴胡【五分(1.5g)】
用法:水煎服。
二、定经汤功效主治探讨
《傅青主女科》中记述“妇人有经来断续,或前或后无定期,人以为气血之虚也,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!”因为前人多认为月经先后不定期是气血虚弱所致,疾病多在肾经,而傅氏认为月经先后无定期并不只是“气血亏虚”这一方面的原因,也有因“肝气郁结”而致病者。
后又补充到,“夫经水出诸肾,而肝为肾之子,肝郁则肾亦郁矣。”此处的“郁者”,积聚也。如《管子·中匡》中有“郁浊困滞”的记载,即“不通也”,可见“郁”应是郁滞、郁结、不通畅之意,应是实证无疑。此处的肝郁、肾郁均应是气机不疏之郁结停滞,而并非是虚弱之象。
从五行学说来看,肝肾乃是子母之脏,子(肝)脏有病,自然可以传之母(肾)脏,最终形成母子同病——肝肾同郁。原文中,傅氏并未提及此时的肾气、肾阳已现衰象。
下文中又记述,“肾郁而气必不宣,前后之或断或续,正肾之或通或闭耳”。从这可以看出,傅氏是在强调因肾郁而致使气机宣降作用失常,从而影响到了冲、任二脉以及胞宫的生理功能,即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“肾-天癸-冲任-胞宫轴”的正常生理功能受限,从而导致月经的先后不定期。
由此可见,傅氏当时创制定经汤的本意并不是针对“肝郁肾虚”这一病机。既如此,那为什么定经汤方中要应用大量的补肾之品呢?傅氏在书中给出解答——“殊不知子母关切,子病而母必有顾复之情。”所以,虽说肝气郁闭,肾气不一定亏虚,而之所以在定经汤中佐入补肾之品是要防止出现“子盗母气”的情况发生。
肾者,为封藏之本,主闭藏精气。肾中精气又是天癸的来源,天癸作用于人体,推动着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机能,肾阴肾阳为各脏腑阴阳的根本,故肾的精气阴阳若有耗伤,多可影响全身或累及他脏。而且肾的病证多见虚证而少有实证,所以有“肾无实证”、“肾多虚证”的说法。
基于上述考虑,傅氏在从肝论治的同时,在定经汤方中加入补肾之品,未必是因为肾气亏虚,而是考虑到肝肾的子母关系与肾多虚证的种种因素。此方中加入菟丝子、大熟地、山药等补肾之品,不单单是在于针对肾虚,而是在于截断病情的进一步深入发展,以达到更快、更好地治疗疾病的目的。
通过反复研读可以理解,傅氏创立定经汤的初衷并不是针对肝郁肾虚的病机,而是在疏肝的同时,加以补肾之品,兼顾子母关系,以达到未病先防、既病防变目的。同时这一治病理念也体现了“治未病”思想。“治以疏肝,佐以补肾”亦符合《黄帝内经》中“治未病”的思想。可见傅氏深得《黄帝内经》之旨,加之“肾易虚”的生理特点,在方中加入补肾之品可谓是神来之笔。
因此,对于月经先后不定期之证,“治法宜疏肝之郁,即开肾之郁也,肝肾之郁既开,而经水自有一定之期矣。”这也是的定经汤应用要旨之所在。
三、定经汤方解
菟丝子、熟地:菟丝子补肾养肝,熟地滋阴补肾,配伍使用补肾益精,养冲任。
当归、白芍:养血柔肝调经。
柴胡、芥穗:既可疏肝解郁,又可理血。
茯苓、山药:茯苓甘淡性平,合山药健脾。
总体而言,定经汤有“疏肝肾之气,补肝肾之精”的功效。
四、定经汤配伍特点
此方立法周全、用药恰当、配伍精妙、补泻得宜是该方的显著特点,不仅体现在药物组成上,更体现在药物用量上。
方中当归、白芍、菟丝子重用至一两,熟地、山药各五钱,此五者味厚而质重,阴药也,补养肝肾精血,性沉静而主阖;白茯苓三钱,荆芥穂二钱,柴胡五分,此三者气薄而质轻,阳药也,疏散肝肾郁滞,性流动而主开。
正如傅山先生所言:此方舒肝肾之气,非通经之药也;补肝肾之精,非利水之品也;肝肾之气舒而精通,肝肾之精旺而水利,不治之治,妙于治也。也就是说,定经汤可以舒解肝肾之气,却并非通经的药,补肝肾之精,也并不是利水的药,但是却可以使肝肾气舒且精通,从而达到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的作用。
五、定经汤拓展应用
在现代临床中,“定经汤”还用于治疗月经后期、稀发、闭经、不孕等疾病。因为这些疾病的根本发病原因多在于肾水不足,水不涵木,木燥烁精,肝肾既为母子,则息息相关,“定经汤”乃滋肾舒肝,阴阳并调之剂,故皆可根据患者的证候特点在此方的基础上加减治之。比如,临床上用来补血养血的四物汤、或者用来疏肝解郁的逍遥散,对于疗效不显者,投此方加减使用,可有明显效果;当患者出现烦躁易怒时,可加丹栀;若患者精亏严重,也可加枸杞、杜仲。
六、从定经汤解析傅氏调经思路
1、经本于肾,不忘补肾
从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关于月经的记载中可以发现,肾在月经的产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傅氏秉承这一观点,认为“经本于肾,经水出诸于肾”,也就是说,月经的产生始于肾功能的启动,肾的功能正常与否是月经能否正常来潮的关键。因此,《傅青主女科》中关于调经的治疗特点和原则之一为补肾法。
2、从肝论治,疏肝养肝
我们说妇人之病,瘀者居多,肝瘀是导致妇人疾病的重因素。傅氏继承刘完素“天癸既行,皆从厥阴论治”的思想,十分注重肝在女性月经中的作用,认为“女子以月经为先天,调经重在疏肝理气,调理气血”,并且傅氏善用疏肝解郁法进行治疗。同时,傅氏考虑到“肝藏血主疏泄,体阴用阳,以平为期”。因此在临证运用中,不单纯“平肝、疏肝”为主,而是强调了“养肝血”为前提,在此基础上可少佐疏肝之品。
3、乙癸同源,扶正解郁
傅氏在调经理论中强调了“疏肝之法当在扶正养阴基础之上”的思想,重视乙癸同源、肝肾同治,即疏肝平肝寓于养血、填精、益阴之中。同时其治疗思想还兼顾到“见肝之病,当知传脾,故先实脾”的“治未病”思想,也是扶正的体现。
4、不损天然之气血,便是调经之大法
傅氏在用药和治疗上,主张“不损天然之气血”,强调“有所不为”,对后世临床有很好的指导作用。用药的有所不为方面,比如调经-血崩篇中的药方,多以扶正祛邪为主,以平补肝肾为宗旨,对于伤经损血之药的应用十分谨慎,即便应用可不会很峻猛,且极少用好补气血之品。治疗上“有所不为”方面,傅氏认为不是所有的月经不调都需要治疗,比如对于经水数月不行之证,他发对不加辨识的过度治疗。
七、调经七法
1、清热泻火凉血法:清经散——经行先期、经量甚多。
2、养阴清热法:两地汤——经行先期、经量少。
3、补中温散法:温经摄血汤——经行后期、量多。
4、舒肝解郁法:定经汤——月经先后无定期。
5、健脾益肾法:助仙丹——经水数月一行。
6、补肝通郁散风法:加味四物汤——经水忽来忽断,时疼时止。
7、补血益气引血归经法:加减四物汤——经量过多。
[声明:本网站所有内容,凡未注明来源为“转载”,版权均归巢内网所有,未经授权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,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,授权转载时须注明“来源:巢内网”。本网注明来源为其他媒体的内容为转载,转载仅作观点分享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版权,请及时联系我们]